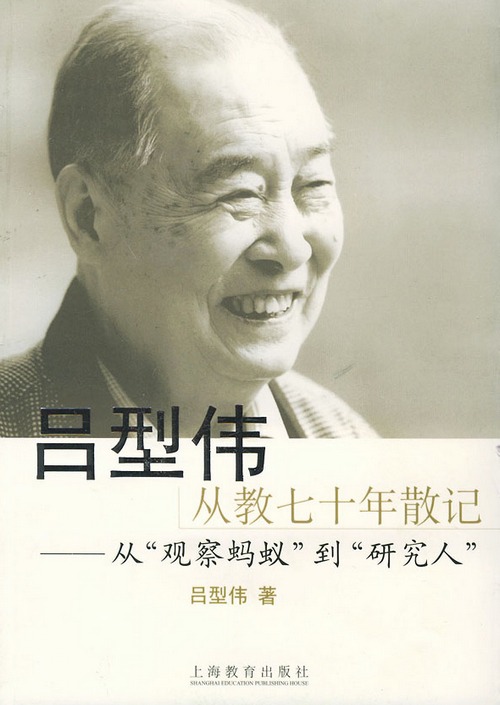|
被称为教育的“活化石”,引领了一个时期的中国基础教育。直至耄耋,思想仍在前沿,他戏称因为70岁闯过鬼门关后,又拥有一次生命
吕型伟:在教育世界里活了两辈子
吕型伟85岁时家中留影。崔益军 摄 ■本报记者 沈祖芸 7月17日,上海华东医院。著名教育家,原上海市教育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吕型伟完成了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所有使命,安静地离开了,享年95岁。 获悉吕型伟过世的消息,上海市教委巡视员尹后庆十分悲痛,当年吕老提携后生的情形又一幕幕地出现在眼前。他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样一段缅怀吕老的文字:“他是一位把人格魅力、生命感悟和精神追求完臻地糅合成教育睿智的世纪老人。从独自撑起一所乡村学校到运筹跨越世纪的教育变革,他始终在宽广的现实背景和历史跨度中,用思想引领实践,用行动把握未来。” 吕老是一位豁达宽广的人。在他的晚年生活中,每每精神矍铄地出现在大家面前,并思路敏捷地引领着教育前行方向的时候,大家都会感慨:一位耄耋老人的思想为何如此前沿?而吕老也总是风趣地回答大家:“我是拥有两次生命的人,70多岁时突发脑溢血后,医生从我的脑袋里‘放了血’,被‘洗了脑’之后的我出现了一连串的‘新现象’,黑头发长出来了,老花眼不见了,吃得下、睡得着,仿佛回到了年轻时代。”话音刚落,全场掌声,大家在感佩中寄托着无限祝福:“愿您在教育的世界里,精彩活上两辈子”。 传奇的教育人生 吕型伟常语出惊人,他常说:“人云亦云不云,老生常谈不谈。否则怎么出思想、出人才?” 1918年,吕型伟出生于浙江省新昌县大明市镇藕岸村,父亲早早去世,靠母亲一人维持生计。但这位乡下母亲却非常有眼光、有见识,她咬紧牙关也要供孩子读书。 8岁,吕型伟入小学;13岁,考取了浙江省新昌中学。他从小就喜欢阅读,读中学时,校长见他喜欢读书,干脆就把学校图书馆交其管理。于是,他几乎是在图书馆里度过了自己的中学生涯。 “那时,我们不想考高中,我们想到苏联去,1935年看到邹韬奋写的《萍踪寄语》,我一看,世界上还有那么一个好地方,三个人说好了,找个工作筹点钱,从新昌步行到苏联去。于是我去办了一个小学,那时我17岁。” 17岁的吕型伟才初中毕业,就只身一人来到白岩村的山沟里,经过挨家挨户地上门宣传,居然招到了81个学生,借了一座破庙作校舍,办起了白岩小学。学生最小6岁,最大的18岁,比吕型伟这个当老师的还大。吕型伟说:“是我办的,我就当上了校长,但是这个校长是没人可以领导的,就是我一个人,校长我当,教师也是我当,烧饭也自己烧,打铃也自己打,就是这样一个大校长。” 一年以后,吕型伟终于明白走路去苏联的想法是幼稚的,而且感觉自己这个娃娃校长当得也不太像样,于是有了进一步求学的念头,但教育救国的思想却深深地扎下了根。 “我的经历中唯一与众不同的一点,就是先当校长,后当教师。”1946年吕型伟大学毕业,来到了上海,他在地下党开办的省吾中学教书,并加入了共产党。 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,吕型伟奉命与教育家段立佩一起去接管国民党势力很强的市东中学。当时,全市有26所公立学校,其中市东中学的政治情况最复杂。校长姜梦麟是国民党上海市三青团的头面人物,每天坐着黑色汽车威风凛凛地出入学校,保镖带着手枪跟在后面。 后来,姜梦麟投降,但国民党不少骨干分子依然隐藏在师生中伺机作乱。6月30日,段立佩、吕型伟正式上任,接管大会开得很顺利,那天吕型伟穿了一套西装,坐在底下的师生都很诧异,为什么共产党派来的校长没穿军装呢?谁曾想眼前这位校长可是从浙江大学师范学院毕业的高材生,年仅30岁的吕型伟早在14年前就当上了校长,只不过那时是自封的,现在可是陈毅市长任命的。 当进步力量逐渐控制了局面之后,就开始公开建团、建党,要求进步的学生越来越多,上海的中学中最难攻克的国民党堡垒被完全攻克,获得了新生。 上世纪50年代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,吕型伟没日没夜地搞教改,抓质量,亲自上课示范。当时因为学校容量有限,为了让更多的劳动人民子女上学,吕型伟费尽心思,创造了一种“三班两教室”的办学模式,就是用30个教室招收45个班级的学生。每个学生一周有两天全天上课,另有4天是半天上课半天活动,这样既能用足校舍,又能保证教育质量。结果这一做法迅速在全市推广,全市在不增加校舍的情况下,多招收了近1/3的学生。吕型伟在市东中学当了7年校长,使这所学校成为上海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。 吕型伟回忆说:“我的学生统计起来大概上万吧,有两点:第一,我还没发现在‘文革’中上窜下跳的学生,第二,到现在为止,我还没发现成为腐败分子的。我培养的学生基本能做到堂堂正正做人、实实在在做事。” 当校长出了名的吕型伟1956年起被调到上海市教育局,做市教研室主任、普教处处长,一直到副局长。有人替吕型伟打抱不平,这么有才干的他为什么官没有做得更大些?有人说他生不逢时,因为“文革”结束时吕型伟已60岁了,也有人说他个性太强,得罪了不少人。吕型伟自己却说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把手都在抓政治运动,我倒是有机会一直在搞教育改革,这反而好,我首先是个教育工作者,而不是官员。他深入基层培养教师,手把手地辅导他们,像于漪、高润华、袁榕、倪谷音等这些全国著名的教师、校长,都是吕型伟发现并一手培养起来的。 吕型伟常说:“我这个人喜欢动,在位的时候也喜欢往下跑,办公室不太坐的,走到哪里讲到哪里,在大大小小会议上讲话,人家也喜欢我讲,讲真话、实话,不讲官话、套话,讲的都是业务上的事,所以我觉得我是个业务干部,不是政治干部。” 吕型伟喜欢说话,忍不住就要表态,他说话有人爱听,也有人不太爱听,因为他常语出惊人。他常说:“人云亦云不云,老生常谈不谈。否则怎么出思想、出人才?” “文革”结束以后,中国教育迎来拨乱反正的“春天”,百废待兴。1978年冬,吕型伟以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的身份到法国访问,以后接连去了日本、美国考察。国外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和技术拓宽了吕型伟的眼界和思路,他把课堂教学称为传播知识的第一渠道,将课堂教学以外的信息渠道称为第二渠道,提出二者应该并重,于1983年发表一篇题为《改革第一渠道,发展第二渠道,建立两个渠道并重的教学体系》的文章。 文章发表后,引起了轩然大波。从上海市到教育部,不少教育界的领导公开表示反对。吕型伟又写了一篇《再论两个渠道》,寄到教育部主管的理论杂志《教育研究》。主编拿到文章,不敢做主,请示刊物主办单位中央教科所的所长。所长看了后说:“老吕是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,我也是副会长,我没有资格审查他的文章。”主编只得又将文章送给分管刊物的教育部副部长,副部长觉得文章没有错,但不便表态。绕了一大圈,最后主编狠狠心:发!文章一发表,立即引来一番争论。 当时,从黑龙江到海南岛,学生念的是一样的教材,考的是一样的题,叫做“一纲一本”,下面无权改动。吕型伟觉得,中国各地发展极不平衡,用同样的课程和教材来教,又用同样的考题来选拔,显然不科学。当时他担任全国教育部课程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,在一次讨论全国课程教材的会上,他正式提出了“多纲多本”的主张,当场就有人反对。他坚持自己的观点,据理力争。最后达成妥协:搞“一纲多本”,即教育部制定统一大纲,在大纲指导下可以编多种教材。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,教材可以自己编,但高考还是全国命题。如此,新教材怎么编?编了谁敢用?吕型伟为上海教育作出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想方设法争取到了上海高考自主考试权。到2002年,上海获得高考独立命题权17年之后,北京也加入了高考自主命题的行列。至2006年高考,全国共有16个省市试行自主命题,占居全国省份的半壁江山,“全国一张卷”的局面被彻底打破。吕型伟敢为人先、敢于探索的精神,在中国教育界有口皆碑,正是其开放且包容的胸怀,刚毅且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,有力地促进了上海乃至全国教育的发展,可以说上海的教育史铭刻着吕型伟浓厚的个人印记。
现在是地球变暖了,人心变冷了。德育是未来教育的最大难题,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担心,是个国际性的问题。 虽然这位人称当代基础教育“活化石”的老人,早在20年前就离休了,但吕型伟仍一直活跃在中国基础教育的阵地上,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在思考着中国基础教育何去何从的问题。 吕老对教育的研究是从研究蚂蚁开始的。 他从小就喜欢研究蚂蚁,后来从事教育工作,就开始观察和研究人的特性了。蚂蚁当然不能与人相提并论,但蚂蚁很聪明,它同人类一样,是一种组织严密的社会化动物。作为教育工作者,研究对象就是自称为万物之灵但又未脱动物共性的人。人类一贯妄自尊大,不愿意把自己同小动物混为一谈,但往往被自己营造的光环所迷惑,使教育步入歧途。比如当前的独生子女现象,家长们认为他们的孩子个个都是天才,长大都能当总统。但如果我们能还人类特别是儿童一个本来面目,我们也许会更客观、更理智地认识儿童,从而使教育工作更符合客观规律,更有实效。 他说,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使教育正面临重大而深刻的复苏。一种崭新的教育将在世界诞生,从而取代产生于工业时代一直沿用至今的教育模式。这种新教育模式将建立在两个全新的基础之上,其一是信息技术,其二是脑科学。一个是教育的物质基础与外部条件;一个是人类对自身的发现,可以说是内部条件。两者结合,将使教育产生一个飞跃,最终使人的潜能得到极大开发。 他认为,人们只知道有金矿、银矿,却不知道还有一个深不可测的、比金银更宝贵的“脑矿”。21世纪教育的最高目标就是使“脑矿”得到最有效、最充分的开发。人脑有140亿个神经元、9000万个辅助细胞,能储存1000万亿信息单位,相当于5亿册图书。显然,这个矿目前远未得到开发。人除了大脑,还有一双被科学家称为“第二大脑”的手。就是这两个器官,使人类与其他动物拉开了差距,值得好好研究。 当谈到未来教育发展问题的时候,吕老最担心的总是德育问题。 他有这样一段话让人印象深刻:“现在是地球变暖了,人心变冷了。德育是未来教育的最大难题,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担心,因为这是个国际性的问题。如今人类可以享受科技带来的成果,可以让飞天不再是梦想,可以克隆自己的生命,但是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,那就是德育。目前人类的道德不是在进步,而是在滑坡。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,我总是想我们的教育成果到哪里去了?” 他认为,十几年来,我们的德育工作效果不明显,主要原因是德育工作者观念保守,对道德内涵的理解太狭隘,而且充满功利主义思想,忽视了有深厚积淀的人文精神基础;方法简单,形式主义与浮躁现象充斥,满足于短期效益。 他风趣地打着比方:你们见过农村田地里用的薄膜吧!外面天寒地冻,里面温暖如春,薄膜为农作物创造了适宜的生长环境。德育工作也是一样,要给孩子创造适宜的好环境,要营造人才成长的小气候。可以从一个人、一个家庭、一个学校、一个社区入手,营造一个优良的小环境,就像大棚一样,让“小气候起大作用”。 近年来,吕老一直在思考创新的问题。他说,在改革与发展的大潮中形式主义与浮躁的现象相当严重,我称之为浮肿病与多动症,口号不断翻新、模式层出不穷,仔细去检查一下,除了向你展现那一点形象工程以外,大都是文字游戏,其实一切照旧。我也曾说过这一场教育改革如果最终失败的话,原因大概就出自上面讲的两种病。病因是多样的,有的是为了出名,有的是出于无知,好像田径运动员,不知道世界纪录是多少,却自吹自己破了世界纪录,岂不要让行家笑话? 基于这样的忧思,他向时任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顾泠沅建议,希望参与教育部重点课题“面向未来的基础教育学校研究”课题组的同志要学习一点教育史,主要是教育思想史,特别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代表作。 他常常感慨地说:“我虽然也努力学习教育理论,也努力在第一线实践,并力图有所创新,但现在回过头看,真正创新的、超越前人的几乎没有,我只是不停地学习、实践、探索,在传统派与现代派之间摇摆,如此而已。我深感进入信息时代与脑科学时代,教育肯定会有重大突破,从理论到实践都会有所突破,可我已没有机会了,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这一代,希望你们第一要学习,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;第二要实践,要自己去办学;第三要多调查,多到处看看;第四要关心社会的变革与其他科学的发展,“教育思想常常出在教育以外”。
他的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后辈晚生,他的生命在更多有理想、有抱负的人们身上延续。 一个教育工作者最大的生命价值是什么?就是他的思想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后辈晚生,就是他的生命在更多有理想、有抱负的人们身上延续。吕老就是这样一位令人高山仰止,却又永远让人去学习和追随的教育家。 在吕老晚年,他将自己横跨5个“五年计划”的教育部重点课题“面向未来的基础教育学校”交到了顾泠沅手中。顾泠沅感受到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和使命感,他不敢懈怠地继续前行。 说起吕老对他的影响,这位上海教育功臣动容了。他说,首先是堂堂正正做人,实实在在做事。吕老强调人的自主创造精神,认为不能在物欲和规范之间,泯灭了人的创造与个性。我曾经问过吕老这样一句话,“你有过仇人吗?”他说:“没有。”我知道,他在“文革”中也有过委屈,但他付之一笑。吕老为人为学的指标,可谓“和而不同,为而不争,宠辱不惊”。 其二,把教育事业和做学问联系在一起。当前的教师队伍,吕老的评价是“三有三少”:“有专业,少文化;有学科,少功底;有责任,少魅力”。在中国教育发展的节骨眼上,吕老都有自己的说法,疾风所至,锐不可当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,就提出“开发潜能,发展个性,教育社会化”的主张。针对教育界的形式主义与表面文章,吕老形象地指出三点,“浮夸、浮躁、浮肿”。对一些所谓素质教育的做法,吕老讥之为“多动症”,提出“基础教育必须返璞归真”的主张。他的文章不长,但都是干货。面对新世纪的中国教育,他指出其三个方面的症结,“应试至上;道德危机;人才出不了”。在教育部会议上语惊四座,“发展是硬道理,但硬道理也得讲道理不是?”吕老不赞成教改上搞“一刀切”,他认为,“学校教改应该是多样化的、原创的、立足自身的”。不规定预定的路线图,提倡“摸着石头过河”,不赞成盲目跟风。 其三,读书与云游。吕老做学问和我们不一样。两个特点:一读书,二云游。看很多书,野书和闲书,广读博览。80岁以后,仍然把读书看作人生的第一乐趣。吕老读书,并不拘泥于教育,从经济到文艺,广泛涉猎,寻找教育灵感。他说:“校长要具有教育思想,工夫在教育学之外。”前些时间,吕老还在研读两本书,《不确定性的科学》和《教育学的迷茫》,还在思索,如何从教育制度的视角去分析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创造力。 其四,豁达乐观的胸怀。在吕老90岁高龄时,医生不允许他出来,但他还是喜欢去学校。关于他的长寿,吕老有段诙谐的说法:“为什么长寿?第一,是要睡过棺材;第二,是开过颅。”当年在安徽搞土改,没地方睡觉,吕老是在一口棺材里睡过觉的。睡过了,就不怕了。前几年,吕老曾经做过一次脑外科手术,脑袋上凿了一个筷子眼大的小洞,手术很成功。关于中国教育改革,吕老认为,教育是一个“不确定系统”,提出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然后说,“摸着石头过河,那么,石头在哪里呢?”他用风趣幽默的话语提出了最关键的问题。回答别人提问的时候,吕老用这样的三句话来概括自己的一生:“我做过一些有益的事;我做过不少蠢事,一些错事;我还在探索。”吕老说的探索,不是空话,他研究教育史,注意到了教育史上的“钟摆现象”,找出了几组核心的矛盾,给出自己的结论——“在四对矛盾之中,寻找中间地带”。 顾泠沅的感悟代表了很多教育工作者的心声。吕老的为人为学,意境深远,理论恢宏。继往不守成,创新有所本,一个有生命的思想在延续,生生不息。
上世纪50年代首先提出创办工读学校。 1978年,在上海重建青少年科技指导站。 1979年,针对中等教育结构单一的弊病,提出应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,并在上海办起七八十所职校。 上世纪80年代,在上海南汇等郊区县开展农村教育改革探索,提出“农(业)科(学)教(育)统筹,成人教育、职业教育结合”的观点,被中央接受。 上世纪80年代初,提出健身体育,反对单纯的竞技体育。 1984年,为了配合课程改革,为上海争取了高考自主权。 1984年,建议把“三个面向”作为教育的指导思想推向全国。 从1985年始,探索面向21世纪的教育模式,逐步在全国18个省市建立了教育试点示范学校,开展实验近20年。 1991年,提出 弘扬传统美德的口号。
怀念我和吕老的深厚友谊 ■顾明远 17日上海来电话,说吕老去世了。我先是为之一惊,然后感到无限悲痛。我们失去了一位睿智的教育家,一位良师益友。虽然早已知道他近年来身体欠佳,常住医院,但总想他这样乐观豁达的人一定能战胜病魔挺过去,没有想到这么快就离我们而去。痛哉!哀哉! 去年12月19日,我到上海华东医院去看望他,那时他精神很好,说自己没有什么毛病,但医生不让他出院,只在节假日回到家里。他的床头柜、窗台上摆满了书籍和报刊杂志。他什么书都看,一直感叹住在医院里“寂寞啊,寂寞啊!”吕老本来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,一生为教育奔波,过了耄耋之年,还领衔未来教育综合改革的课题,他从南到北,从东到西,具体指导学校的教育改革。现在把他关在病房里,哪能不让他感到寂寞? 我和吕老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初,那时他是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,我是学会的学术委员,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。特别是1986年春天,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组织师范教育代表团到日本考察,吕老是团长,我是副团长,一个多星期的一起生活使我更加认识了这位睿智、豁达、风趣的教育家。他会给我讲许多他经历的故事:他17岁中学毕业就在家乡浙江的山区学校当校长,后来上了浙江大学,参加了地下党。他会告诉你,解放前夕怎么巧妙地与国民党作斗争。他还会告诉你,解放后他曾带领上海的教师去参加土改,因为没有正式的住处,曾经一个人住在寺院中的寿材里,他风趣地说,“我是睡过棺材的”。说到风趣处,让你忍俊不禁。 大约是上世纪末,他在家乡新昌参加母校的校庆,忽然头晕,说话也语无伦次,去医院发现头颅渗血,经过引流、清洗,很快就恢复了。他病后照样到处跑,看见我们就说:“我是被洗过脑的,现在新头发又长出来了!”他就是这样一个乐观风趣的人。 吕老是一位教育思想家,他对教育有三句极为精辟深刻的话,他说:“教育是事业,其意义在于奉献;教育是科学,其价值在于求真;教育是艺术,其生命在于创新。”多么精辟! 吕老是一位教育实践家,他一生就是在践行这三句话,吕老七十多年来,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校的实践,他担任过小学教师、中学校长、教育局长,从事过教育研究工作,而且作出了卓越的成绩,为我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。 吕老是一位教育革新家,他总是走在时代的前面,提出许多教育革新的思想。他常常讲,教育是未来的事业,要向前看,考虑未来的教育。他把他的两本教育文集都起名为《为了未来──我的教育观》、《一生为未来》,充分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。 我和吕老有着深厚的友谊。可以说,我是在吕老的信任、指导、帮助、支持下成长起来的。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编纂《教育大辞典》的工作。1986年11月5日至9日中国教育学会在武汉召开学术会议。会长张承先、副会长刘佛年和吕老提出编纂一部教育大辞典,并且提出让我任主编。我开始不敢接受,怕不能胜任。他们认为此项工程巨大,需要年轻力壮的学者长期努力完成,因而鼓励我把这个重任担任起来。这部书从分卷到增订合卷本共用了12年的时间。吕老作为领导小组成员,大辞典每次开编委会、审稿会都来参加,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,使《教育大辞典》顺利完成。 2000年中国教育学会因张承先会长年事己高,身体欠佳,需要换届。又是吕老一再建议我来担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。这十多年来,他经常参加学会的活动,不仅给学会活动给力添色,而且是对我个人的极大支持。我们虽然年龄相差十来岁,但真算得上是忘年之交,我们不仅有相同的教育实践经历,而且我们有共同的教育理想和教育理念。我们的友谊就是建立在这种共同信念的基础上的。现在吕老走了,我们悲痛,但是寿无金石,我们只有努力工作,薪火相传,使吕老的精神永存。 (作者为中国教育学会原会长,北京师范大学教授) 《中国教育报》2012年7月20日第3版 (责任编辑:admin) |



 教育主张
教育主张